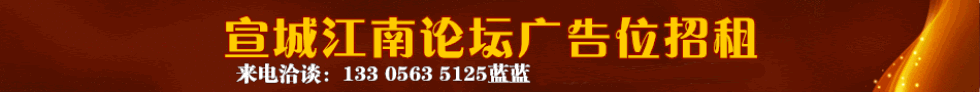|
|
母亲年轻时,做得一手很好的针线活,挑花绣朵,样样精通。记得我曾经戴过一个虎头帽,围过一个餐围,都是母亲绣的。只要货郎一进村,货郎鼓一响,她就凑上去,拿鸡蛋与货郎鼓大爷换七彩丝线。货郎鼓大爷渴了,要口水喝,她立马拿出大陶壶,为货郎鼓大爷冲水。货郎鼓大爷也很爽快,立马给妈几根绣花针。这种物物交易,看似商品交换,其实更是人情传递。
念书五六年级那几年,母亲身体极差,住校周末回家取米,没有米就得拿玉米磨玉米碎,妈妈不能磨,我只能自己去人家借腰推磨,一圈一圈地挨着磨,自己筛好带去学校,交与工友,工友师傅看我困难,便与老师商量行便。好在我从小读书还算不错,老师工友都照顾我,害得老师和同学都跟我吃掺了玉米碎的饭。一个星期就靠一菜筒腌菜,夏天,菜都长了毛,只能就着热饭拌一拌继续吃。
过去,乡村有一种手艺人,叫接犁头补锅的,一副担子,一头挑着个风箱,一头是只火炉。到了一个村子,往稻场上一坐,把风箱与炉子接起来,谁家补锅,就先拿点炭来。风扇一拉,炉火通红,生铁一化,把融化的生铁往锅洞处一倒,上下一按,锅就补好了。生产队里接犁头也是一样,先化铁,然后把融化的铁往模子里一倒,把旧犁头往模子里一插,一会冷却了就好了。如今的乡村里,基本看不到这些了。社会虽然进步了,但记忆里这些往事,却是那般的深刻,时时提醒着我们,永远不能忘记好日子来之不易。
|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