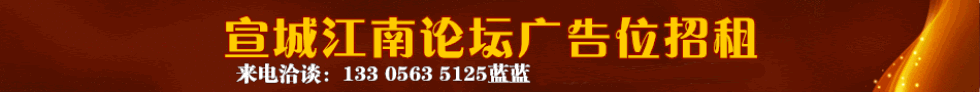|
插队来到农村当农民,接受再贫下中农教育,那时才知道要吃苦了,一开始,我们插队小组一共是三个人,刚插队时没有住处,是社员屯出自家的小披屋给我们住,下雨时外面下大雨,家里下小雨,外面不下了,家里还在滴滴答答,床上只得用塑料布遮盖,后来人家要用,生产队就安排我们住进了村后面的牛栏屋里,、、、、我们的邻居是生产队里的十几头牛,那个味道,再加上晚上,那十几头牛擦痒痒,一片牛栏架子的嘎嘎响声,使得你无法入睡,还担惊受怕。后来,在我们一再的要求下,政府对插队知青在农村的生活情况进行大检查,给我们落实安排,搬到了村子前面的公路边上,生产队的社屋里住,是土墙小瓦屋,房子较大,生产队派人隔了几个房间,勉强住了、、、、、、我们隔壁住的是上海插队知青。后来,按照下放政策,建了三间土墙小瓦屋,算是定居咯。、、、、、、
通过插队当农民一年多的亲身经历,真的晓得了农民真的很累很苦。
在“大合隆”当农民的那段日子,虽然还不算一个合格的农民,但是我经历了,这是一生中最最苦累的一段往事,难忘,难以忘怀。
我们插队的生产队,是个有山有地又有田的山区生产队,山上有树木毛竹茶叶,跟着贫下中农上山砍树倒还行,把树放倒却不那么容易了,首先要考虑往哪个方向倒,这样你才好选择下斧的方向,最有意思且最有危险的是将砍倒的树“放风”下山,山上有“风路”,怎么才能将树安全“运输”到山脚下,这可是门“技术”活了。
因我们插队那是个有山有地又有田的村子,可以说一年四季忙到头没得息的,“丢了犁就是耙”哦。田里的活算用犁、耙、耖是个较为“技术”的活了,看着简单,可你上去试试,一定会懵的,首先,你得跟牛有过交往(放过牛),会使用“牛大师”的“撇啊、浅啊、喻……”等等用语,才能指挥得当,用的得心应手。通过2年接受贫下中农的耐心“教育”,拔秧、插秧、推秧草、割稻、掼稻等这些活当然不在话下咯。基本掌握了要领,工分也涨上去了,对用犁耙也还说的过去,耖上的活还有点“夹生饭”,就是从哪里下耖和望不准哪里要拎起哪里要往下按,不是这里有坑凹就是那里像土包,耖不平。不过在全大队插队知青中,我干的农活技术算前茅的了。
茶叶收入也是我们生产队的经济来源之一,可以说。有茶山有田的地方,在茶季里是最忙的了,男劳力白天整田插早稻秧,晚上又要熬夜制茶。采茶、卖茶全部都是赶季节的事,那时候这个季节里学校都放农忙假,真是男女老少齐上阵,人们干的却很欢快,山上采茶歌唤起田里插秧哥,真有点“刘三姐”电影中对山歌的那画面。茶季里有苦也有乐。
还有那些在山上挖茶棵、挖包谷地,烧砖瓦窑、石灰窑……等等等等,数不胜数。所有这些活计,都尝过干过,具体当农民的生活过程,待以后在【茶余饭后】再叨叨。唉、、、、、、那个苦和累、、、、、、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