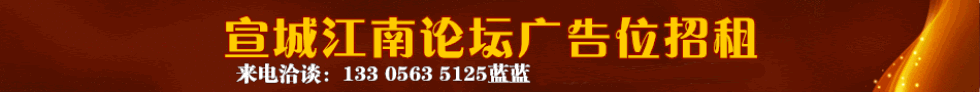|
|
 发表于 2025-2-1 20:01:22
来自手机
|
显示全部楼层
|阅读模式
发表于 2025-2-1 20:01:22
来自手机
|
显示全部楼层
|阅读模式
来自 中国安徽宣城
鲜见的冷冬
因为气温最低也就负二度,不能称为寒冷,所以称冷冬较为贴切。
从昨天起天气即一反日前热气升腾的模式,呈阴冷中夹杂着下个不住的滴滴答答的小雨之状态。特别是这气温的突变,为人们营造出过山车般的感觉。
这或许就是天有不测风云的说法之体现吧。因为早些天在户外还来不及地将热烈而累赘的冬装脱离身体,这两天就完全是一副截然相反的样子。气温的骤降使得在室内若不开空调则颇觉不适。
记得六十年代中期在高中阶段,寒假后开学前,校团委、学生会及班级团支部、班委会干部得先到校集中学习。晚上九十点钟回到宿舍,无热水洗脚。我们就用脸盆从敲开冰的塘里打来冷水,再倒进脚盆。看着那浮着冰块的冰水,实在下不去脚。但不洗又不行。几个人只好集体喊:一、二、三,同时咬着牙将双脚踏进脚盆,一股彻骨寒气顿时从脚底徐徐上升。好在上床后,过了些时,双脚就热乎乎的了。不然就算到天亮,这双脚也断然不会热的。
又想起七十年代在蚌埠时,北方来的学生极不适应这边冬季的寒冷。因为南边冬季以往靠煤(如今靠空调)取暖,在不具备以煤取暖的学生宿舍里,北方来的学生许多都被冻感冒了。于是他们就常念起在他们家那儿,冬天如何如何好,在城市有暖气,在室内只穿内衣即可,甚至还可能会出汗。即便在农村,有火炕取暖,非必要无须出门,猫冬的人们只需每天在家吃喝即可。那种享受的感觉,南方人是无法想象出来的。
当时因为冷,有少教学生甚至产生请假回去,待气温稍上升后再返校的荒唐念头(短训班学生都带薪上学)。对于这天方夜谭般的梦幻想法,学校当然是予以严词拒绝!不过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南北气候的差异之大。
不过,其时感觉到的冷与数十年前相比,已是小巫见大巫了。那时即便从头棉到脚,也抵不住阵阵寒气透过棉絮缝隙直刺肌肤。无论白日或是夜晚上床后,双脚被冻掉的感觉如影随形般地紧粘着你。
一九六九年二月初,大雪连下多日,我一个人身背行装前往下放地。那天从棲凤岭(庐城至盛桥途中)下了客车后,与另一同车结识的同伴各拄一木棍,踏着一尺来厚的茫茫大雪迎着寒风蹒跚前行。裤脚及鞋子里都灌滿了雪。在过一水沟时,我们都脱下鞋袜,趟水而过。在过那道龙腾河时,我在同伴示范下,眼盯没入水下的一尺多见方的大方石,先用木棍探实大石位置,再跨出一只脚先踏上去,踩稳后再跟上另一只脚。就这样在冰水里逐一趟过了约十来块大方石。到魏岗公社时已是热汗涔涔。可在当时那个条件是没有地方可洗澡的。
八十年代初,大雪曾将我们所住的平房房梁压弯。为防不测,我们将房顶上的厚雪扫下来。在我上下班的路上,自行车在一尺左右的厚雪中骑不了,只能在路中央被行人踩出的仅10多厘米的窄沟中推行。
就是到了二OO八年前后,我们这还常下大雪。自那以后雪渐小也渐少,到了近几年想见雪已成了奢望。特别是如今的冬季,湿衣服半天即可晒干,这在以往可是想也不敢想的事。
这气候变化太大,冬季气温升高太明显,尽管冬季寒冷会让人感到不舒服,可从长久来看,这暖冬决非好事。这里借用白居易《卖炭翁》中那句“心忧炭贱愿天寒”聊表此时的心境。
如今尤感美中不足的是,此间的冷冬也到了物以稀为贵的程度了。如此看来,唯冬天大寒,接下来的春、夏、秋才会有好日子笑逐颜开地在前面向我们招手。大家看呢。 |
|